中国古代的宇宙观,都来自庄子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庄子似乎是最避世的那一个,人言庄子,总是“无为而治”,远离朝堂,与当今的躺平文化最为契合。但其实,庄子的思想也是最辽阔的。他不思考家国观,只思考宇宙观。
日本学者蜂屋邦夫便着迷于庄子的宇宙观,他作书《庄子》,逐字解读庄子的思想。下文为他解读我们熟悉的《逍遥游》,在他的眼里,庄子所书写的不仅是一种思想,还是当时中国的某种宇宙观。
下文摘选自《庄子》,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北冥(北极之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逍遥游》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仅仅是这个开头,实际上就已经是不合常情的虚妄之谈了。“北冥”指北极的海,“冥”与“溟”同,表示幽暗而没有边际的感觉。这是说,北方黑暗阴沉的大海广阔无际。

关于“溟”,公元三世纪的注释家司马彪解释说:“指南北极。因为距日月遥远,所以名为溟。”虽说是南北之极,但并非我们所知的南极和北极。大地作为一个平面,无限地延展,天空覆盖于其上,日月运行于天空的中央,因此,日月之光不能到达的地方是黑暗的,它延伸的边界亦无从知晓。那里也就是所谓大地之极,太阳所能照耀的大地到此为止,再往前就是“溟”,已经不再进一步追究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论语·颜渊》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语。有人叹息说:“人们都有兄弟,我只有一个兄弟,却还因胡作非为而几将丧命。”孔子的学生子夏安慰此人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意思是既然全世界的人都是兄弟,为何还要哀叹没有血亲的兄弟呢?“四海之内”是指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世界是为四海所环绕的。
大海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开放的,既是游乐之地,也是捕捞大量鱼类、贝类而使人们生活丰裕的区域。当然,海有时也是令人恐惧的,但其形象绝不是幽暗、荒凉的。但是,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海却是远离文明之花盛开的中华世界的晦暗阴郁之域。“海”与月亮完全隐没的漆黑的“晦”相通,了解了这一点,海的形象就相当清楚了吧。
司马彪“因为距日月遥远,所以名为溟”的解释,也接受了上述观点。因此,即使认为在“溟”中有骇人的怪物也不足为奇。
栖息于“溟”之中的名为“鲲”的鱼,据说大到不知有几千里。即使按一里四百米来计算,千里也有四百公里,要是几千里的话,其大小就以一千公里为单位来计算了,说不定有日本的本州岛那么大,这正有所谓“白发三千丈”的意蕴。三世纪的注家崔譔说,鲲就是鲸,但实际上,鲲是鲸所远远不及的。
而且,鲲竟然是指鱼卵,是连小鱼都算不上的鱼子。以此作为巨大无比的鱼的名称,简直就是把别人当傻瓜,但其中蕴含了庄子以至小通向至大的思想。
《逍遥游》篇说,鲲变化而成为鸟。但是,鱼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变成鸟。生活在大陆而与大海无甚关联的庄子,应该不知道有飞鱼之类的事。不过,中国古人相信,鹰变为鸠,鼹鼠变为鹌鹑,腐草变为萤火虫,麻雀入海而变为蛤蜊,等等,这类记载在《礼记·月令》中可以看到。按照这种思路,鲲变为鸟也就不奇怪了。这个鸟就是鹏,即大鹏。
02
从“北冥”飞向“南冥”的大鹏
如果鲲是大得离奇,那么鹏自然也是大得离奇的。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既然鲲的大小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鹏的大小当然也就不知道有几千里了。“怒”是指大鹏奋力拍打翅膀。“垂天”意为天空的一边。大鹏飞起时,它的翅膀把天空的一边都遮盖了。所谓“海运”,是指大风吹拂使海面波涛汹涌,也就是台风或冬季猛烈的季风等狂风大作的情形。此时,大鹏乘着风势从北冥向南冥迁移。
也可以认为,鹏本来就是大风的形象化。“鹏”与“凤”相通,“凤”又与“风”通,这些字有亲缘关系。从猛烈的大风联想到奇大无比的鸟在振动翅膀,也不算非常怪异。
原文对北冥没有任何交代,却特意说南冥是“天池”,这是什么原因呢?撰写《庄子疏》的唐代成玄英说,因为大海和大河原本是自然物而非人造,所以称之为“天池”。照此理解,北冥也是同样的东西。成玄英还说,南方是光明之地,大鹏是从黑暗的北方趋向光明的南方。成疏的这一解释看来是抓住了要害。
就是说,没有“天池”这个解释,南冥就依然不能摆脱因远离日月而幽暗不明的意象。但如果是“天池”,南冥就不再是黑暗的南方尽头,而变成超拔于这个陆地世界之外的广阔明亮的天界之池的形象了。大鹏是超越世俗世界的象征,因此,就必须让它从北方尽头的暗海飞向光明的南方天上世界。
庄子在这里引用了“齐谐”。所谓“齐谐”,有认为是记载怪异事物的书籍之名的,有认为是颇知怪异事物的人的名字的,两种解释皆可通。不过,这是庄子随意虚构的名称。庄子是要据此证明,鲲和鹏的故事并非无稽之谈,同时也是在嘲笑众人那种对表面上有权威的人或书盲目轻信的习惯。“齐谐”的话是这样的: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水击”是指大鹏为向上飞而在水面上拍打翅膀。因拍打翅膀而使水面掀起波浪,波及范围达三千里,这仍然是“白发三千丈”之类的夸张描写。“扶摇”指旋风,原本是形容“呼呼”的风声的词。“抟”,古作“摶”,这里是卷起旋风的意思,具有与團(团)和專(专)相同的语感。“专”是把丝线绕在缠线板上,由此引申出揉成团的意思,例如,使心专一就是把心紧凑地收缩成一团而不散开。“团”也是揉成一团之意,或指球形,亦即圆。
原文说:兴起旋风,乘着风向上飞升,竟达到九万里。这也是大胆的表达方式。这远远超出五百公里的大气层,已经上升到地球与月球距离的十分之一高度。当然,这些数字没有具体意义,不过是讲了一番令人惊异的腾空高飞的大话而已。
“息”是风,“六月息”是夏季的大风。虽然也有把“息”释为休息的“息”,从而将“去以六月息”解为“经过六个月后休息”的。但既然是夸张虚构的描写,就要能动人心魄,从这个角度说,还是“上达九万里的高度,乘着大风翱翔而去”这个解释更好。
03
蓝色是天空的本色吗?
在开篇一通让人为之一惊的虚言大话之后,庄子开始稍作议论: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野马”等句的意义不够明晰。“野马”是指烟霭,即天地之间的气。“尘埃”的“尘”是尘土,“埃”是细微的尘土颗粒,尘埃也可以看作是天地间的气。所谓“生物之以息相吹”,是说天地间的有生之物相互吹气。因此,野马啦、尘埃啦、生物的气息等,大概是指充满天地间的气而言的。在庄子的时代,由于人们对大气的本质还不了解,就认为大气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
大鹏在这大气中掀起旋风而起飞,此时从地上遥望高远的天空,天空是呈现蓝色的。但是,在野马、尘埃和生物的气息中,有使天空呈现蓝色的东西吗?这样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因此,作者发出了疑问:“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意思是:天的蔚蓝之色究竟是不是它的本色呢?或者只是因为无限遥远而看起来如此呢?“所至极”意为至极之所,也就是终点。

明·刘贯道《梦蝶图》
仰望天空就体会到其蔚蓝之色的奇妙,可见庄子的感觉是柔软而敏锐的。《楚辞·天问》以战国时期楚人屈原提出的关于天地自然和人类历史的诸多疑问而闻名,但其中对天空的蔚蓝色也未曾言及。
但庄子了不起的地方还不在于对天空的蔚蓝之色发出疑问,而在于他“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从极高的天空俯视下方,同样也是呈现蔚蓝吧)”的推想。在现代,我们有了人造卫星,也知道从人造卫星上所看到的地球的样子,其颜色正是呈蔚蓝色,如苏联宇航员所描述的:“地球是蔚蓝色的。”但是,在没有飞机、更没有人造卫星的时代,庄子何以能做出这种想象呢?如果鲲和鹏是超乎寻常的构思的话,那么,根据天空呈现蓝色而推测出陆地远看起来也是蓝色,则是极为惊人的想象了。
在眺望广阔无际的天空之时,我们为世俗世界所拘系的心灵有时也会得到解放。从飞机上俯视陆地,会觉得地面上的物体很小,这是大部分人的经验。人们之所以特意不辞辛苦地登上山峰,主要是希望享受精神上的释放感。借助悬挂式滑翔机和滑翔伞而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很多人喜欢的体验,此时,人们头脑中的俗念一定会消散而去。
庄子不是通过实际的身体动作,而是试图通过大鹏飞翔的想象,去实现那种精神的解放。这就是原文中所说的,以高飞于天际的大鹏的眼睛来俯瞰地面,种种世俗之事将会消解于广阔的苍茫大地之中。
对于心灵的超越作用来说,这种状态似乎是必要的。庄子创作鲲和鹏的虚构故事,以大鹏的视角俯视大地,就是想营造这种状态。
04
大鹏起飞的条件
接着,庄子话锋一转,以常识性的逻辑对大鹏起飞的条件进行了讨论。此处是带有鲜明的散文特征的一段,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语来解读:
如果水的深度不够,大船就不能浮起。把一杯水倒入坑洼处,如果是小草,就能像船一样漂浮在水上,但若把杯子放上去就会沉底。这是由于水浅船大的缘故。同样,如果风不够大,是没有承载巨大翅膀的力量的。因此,上升到九万里,风才在下面充分地聚成。然后才能乘着风,背靠苍天,无所阻碍。那时,就将飞向南方。
大鹏起飞需要九万里的大气的量,抛开这一点暂且不说,这段话确实是极具逻辑性的。看上去似乎是荒唐之言,却一变而为所谓正经的议论,庄子的论调是变化自如的。
庄子一方面强调大鹏异乎寻常的巨大,另一方面又安排对照性的存在物登场,这就是蜩(蝉类)和学鸠(鸠鸽类)。蜩和学鸠看到大鹏超常的行为,就嘲笑说:“我振翅而飞,奔向榆树、枋树,有时飞不到那么远,就落在地面上。为什么要上升九万里,然后飞向南方呢?”
蜩和学鸠是极为普通的虫和鸟,它们的活动范围充其量不超出榆树和枋树生长茂盛的区域。它们也是极为普通的众人的代表。众人常常是在日常琐碎的事务上劳神费力,深陷其中,并以此为标准评论他人的生存方式。然而,这只是对他人生存方式的无知。
庄子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出游近郊的人,要准备三顿餐食。吃了这个餐食,返回时仍然腹中饱满。出行百里之外远方的人,前一天要准备捣舂好的米。如果是千里之外,要用三个月时间准备粮食。这种情况,这两个小动物又怎么知道呢(之二虫又何知)?
这就是说,各种行为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因此,“之二虫又何知”一句的意思是,矮小的蜩和学鸠不能理解大鹏的行为。“虫”除虫子的意思外,有时也泛指动物,此处即是此意。古代称兽类为毛虫、鸟类为羽虫、龟类为甲虫、鱼类为麟虫(《大戴礼·曾子天圆》)。依此而言,人类是倮虫。“倮”与“裸”同,即人类是裸露之虫。
“之二虫”是指蜩与学鸠,大多数人都会如此理解。但是,三世纪时整理《庄子》并作注的郭象却解释说:“二虫,谓鹏蜩也。”这里说的“蜩”,无疑也包含“学鸠”。郭象的这个解释实在是很奇怪。其意思是,鹏和蜩都不自觉地各自处于悠然自适的状态,所以没有必要相互批评。这是郭象学派万物皆合于性分而逍遥这一独特思想的体现。但是,认为这就是庄子思想的原意,还是颇为牵强的。
因此,大鹏出于自身的理由而跃升于九万里的高空,然后飞向南方。同样,在世俗中生活的我们,要超越世俗,还是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的。就是说,这个条件才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
05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在将巨大的鹏与矮小的蜩和学鸠作了对比之后,庄子进一步围绕大小的观点展开论说。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知”是指知识和智慧,“年”则是指寿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小知、小年比不上大知、大年,所以,并不是无论大小都各自逍遥,矮小的蜩和学鸠终究是比不上大鹏的。
“朝菌”一词,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指早上长出、晚上枯萎的菌菇类植物,一说是早上出生、晚上死去的虫类。“晦朔”一般意为每月最后一日和第一日,这里是指夜晚和早晨,意为一天。早上出生则夜晚死去,夜晚出生则早上死去,如果仅有如此短暂的生命,当然就无从得知完整的一天。
关于“蟪蛄”,也有几种说法,但作以下解释就可以了:蟪蛄是一种蝉,它春天出生则夏天死去,夏天出生则秋天死去,因此不知道一年有春秋之季。
那么,大年是什么呢?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古代以春秋表示年龄,所以这里春和秋的意思是寿命。这是说:楚国南方称为“冥灵”的东西寿命上千年;上古的“大椿”寿命一万六千年。从以半年为春、半年为秋的观点来说,一般认为冥灵和大椿两者都是树木的名称,但是,树龄达千年的树木,虽然不多见,却无疑是存在的,庄子若是特意将其作为大年的例子举出来的话,似乎有些不恰当。后世,在被认为是明代人罗勉道的注本(《南华真经循本》)中,有认为“冥灵”是冥海之灵龟的说法,此说似乎更好。
至于树龄一万六千年的树木,让人想起屋久岛的绳文杉。无论是冥灵还是大椿,都有所夸张,但没有夸张到像鲲和鹏那样超乎想象的异常巨大的程度。在这里,庄子举出完全可能存在的短命和长寿的生物,来提高鲲和鹏的可信度。即是说,既然异乎寻常的长寿生物是存在的,那么异乎寻常的巨大生物的存在也是可能的。
于是,讨论就沿着如下方向展开:“小年不及大年”,但大年若要自夸则不可取,因为从更大的大年看来,它也只不过是小年。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彭祖是以长生闻名的上古传说人物,其寿命据说有八百岁或七百岁。“匹”是匹敌的匹,为比肩之意。庄子说,人们都祈愿像彭祖那样长寿,但彭祖与冥灵或大椿相比也不过是小年,想成为这样的彭祖,是何其可悲!这个理论最终与《齐物论》篇“莫寿(长寿)于殇子(夭折的婴儿),而彭祖为夭(短命)”的议论相联系。
06
以至极之境为目标
庄子首先豪迈地描绘出鲲和鹏的形象,似乎从大鹏的视点出发超越了陆地上的种种事物,但展开大与小的议论后,稍稍拘于说理。因此,庄子又以“汤之问棘也是已”一句,让大鹏再次登场而转入故事的叙述。原文重复叙述了与开篇故事至蜩和学鸠出场这部分几乎相同的内容。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大鹏故事的异传,不过这个问题在此处是无关紧要的。
汤是殷王朝的创立者,棘是殷汤时代的贤人。《列子·汤问》记载了汤向夏革提出各种问题的场景。“革”与“棘”,古代的发音是相同的。在这个对话中也有关于冥灵和大椿、鲲和鹏的故事。庄子援引汤和棘的对话,大概是要说,自己所述之事也有此文献依据。今天我们看到的《列子·汤问》的篇章,或许倒是根据《庄子》的叙述创作出来的。但是,庄子那个时代有关汤和棘的对话被认为是有其传承的。
我们回到《庄子》。“汤之问棘”故事中的鲲和鹏,并没有被构想为鲲变化而成为鹏,而是被描写成两者皆为巨大离奇之物。而在大鹏跃升九万里飞向南冥时嘲笑它的则是“斥鴳”。“斥”是水池或小的沼泽,“鴳”大概是麻雀之类,斥鴳就是生长在水池或沼泽边的小鸟。与开篇的故事相比,仅有这种细小的差别,其余内容基本相同,并以“此小大之辩也”作结。“辩”是辨别、区别的意思,这里是让斥鴳来体现“小知不及大知”。

在开篇的故事中,围绕大鹏上升九万里而南飞,通过出行目的地与准备粮食的例子指出,不同的行动皆需满足相应的条件。在这里,则以斥鴳的观点为基准而写道: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能)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知效一官”意为其才智仅能担任一官之职。“行比一乡”意为其行为只能感化一乡之人。“德合一君”是说其德性仅符合一位君主的心意。“而(能)征一国”,意思是其能力仅为一国所聘用,“而”与“能”通用。关于这四句的解释,在细节上存在许多分歧,但主要是在批评像蜩和学鸠、斥鴳那样满足于小才能而以自己的理想为至高无上的人,我们在理解的时候首先抓住这一点就可以了。这暗示着,我们众人或许也无非是这样的存在。
“若此”是指斥鴳之类的观点,“自视也亦若此”就是用斥鴳那样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因此,这里是从上文所说的行动及其条件的客观性问题,深入到了自我认识的问题。对人来说,自我是绝对性的,故而满足这个自我是重要的,但若仅以世俗的价值为标准而自我满足,就与蜩和学鸠、斥鴳之类的短见浅识无异了。
此处庄子又安排了一位宋荣子出场。根据各家的解释,宋荣子又作宋钘或宋牼,宋国人,他曾提出人的欲望本来是寡少的、受到侮辱而不以为羞耻等观点,发起反战和平运动。在杂篇最后一篇《天下》中,宋荣子也以宋钘之名出现。庄子大概是视其为本国的先贤,特别关注其“见侮不辱”之说而有所论及。
宋荣子的态度是“犹然(舒缓地)笑之”,与上述的俗人是不同的。“笑之”是嘲笑“自视也亦若此”的世人的自我满足。那么,他的理想境界是何种风貌呢?那就是: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这在《庄子》书中也是名句之一,意思是说,宋荣子即使受到所有人的褒扬,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勉励;即使受到所有人的诽谤,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这的确是超然之境,我们一般人受到赞扬就会喜悦、受到诋毁就会气馁,无论如何是做不到宋荣子这样的。
宋荣子何以能如此超然?那是因为他“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所谓“内外之分”是指自我的精神这一内心世界与自然和社会这一外部世界的区别。划定这一区别,内心就不为外部环境所扰乱。“辩乎荣辱之境”的“荣辱”指荣誉和耻辱,“境”是处境,“辩”是辨别之意,意思是辨别荣誉和耻辱的处境。但辨别不是单单区分何为荣誉、何为耻辱,如果与“定乎内外之分”而保持内心平静这一点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与其说是区分了荣誉与耻辱,不如说是领悟到了荣誉和耻辱都不是应该执着的处境。
虽说大鹏的飞翔是超越世俗世界的象征,但那是寓言,我们不可能直接变为大鹏。到了宋荣子的阶段,才进入人的层面的言说。不为荣辱的处境所影响,这就是超越。这样说的话,我们也就能具体地抓住一个形象。
但是,对于宋荣子的境界,庄子说它“斯已矣”(仅此而已)而不予赞同。他认为,宋荣子的确是“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但是,“虽然,犹有未树也”。“数数然”意为对事物汲汲追求和忙碌追逐,“树”是立的意思。此句是说,宋荣子虽然没有劳碌于世俗之事,但是,仅仅是不劳碌于世俗之事,还不能使他立于至极之境。由此,庄子又举出一个似乎领悟了至极境界的人物,这就是列子。
07
列子的境界
《庄子》杂篇中的《列御寇》篇是讲列子的,但这位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尚不明确,甚至其人物的真实性都有疑问。庄子描写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也是含混不清。
“御风而行”即乘风出行。与宋荣子相比,这是远为超脱于世俗世界的。“泠然”是爽朗轻快的样子,“善”是赞赏之意。“旬”指十天,“旬有五日”意为十天加五天。列子乘着风出行,经过十五天也要返回。有注解说,这是基于十五天后天气和风发生变化而言的。

列子乘风而行的描写,是表现他的状态犹如仙人一般,还是对他不被世俗所束缚的象征性的表达呢?结合上下文来看,似乎更接近仙人的形象。理由是,列子虽被给予“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的评价,但结论是他“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致福者”是指给人带来幸福的各种事情。对于这些好事,列子是“未数数然也”,不劳心费神去追求。“免乎行”就是免于步行的烦累。列子是乘着风游行,所以不需要走路。也就是说,列子被描述成如仙人一般。“所待”意为依据、所依赖之物。列子不会汲汲追求幸福,也不需要步行,但要出行则不能没有风,出行经过十五天,风发生变化,就必须返回。在这个意义上,他仍然有风这种需要依赖之物。列子走在相当正确的路线上,但并非是完美无缺的。
那么,达到至极之境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庄子说:
若夫(说起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这样的人还将)恶乎待哉!
“天地之正”指天地自然之道,乘着“天地之正”就是与天地自然之道完全同一。这样的表述实在是有些抽象,但也是庄子所擅长的。此处所言,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
关于“六气”一词,有多种解释,认为是指阴、阳、风、雨、晦、明之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还有认为是指天地和春夏秋冬之气等说法。“辩”是变化的意思。所以,把“六气之辩”理解为因气而发生的天地自然的一切现象,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达到至极之境者与天地自然之道同化,故能制御天地自然的一切气的现象,游于无穷尽的境地。这种境界虽然不像列子那样需要依凭风,但总觉得有些仙人的意味。“游”就是悠然自得地委身于那个境界之中,这样的人已经不依待于任何物。这才是庄子所设想的至极的存在。
本文摘编自

《庄子》
作者: [日] 蜂屋邦夫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副标题:迈向超俗之境
译者:张谷
出版年: 20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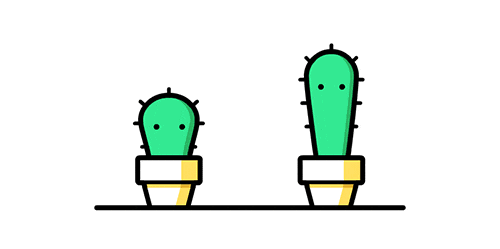
编辑 | 轻浊
主编 | 魏冰心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