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吧,出发的时刻到了”

在网络平台中,记录异乡生活的视频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播放数据,比如去亚马逊雨林感受生命的野蛮生长,在肯尼亚远望象群……或许是因为这样充满激情的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望而不可求,更多人的生命日常或许是在平平淡淡中趋近无聊。
生活是平淡的,但对生活的感受可以不是。在彼得·汉德克笔下,时间都放缓了流速,微不足道的日常中满是对细节的观察,无波无澜的一天也有细腻的感受。下文是他即将开启一段旅途时的情形,和他一起走吧,“出发的时刻到了”。
本文摘编自《内陆之行》,经出品方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故事的开始
故事开始于盛夏的一天。
到了这个季节,当你一年里第一次光脚走在草地上,蜜蜂就会蜇到你。一直以来,这事至少发生在我身上。这期间我得知,你第一次,甚至一年里就这么一次被蜜蜂蜇的日子恰好就是洁白的苜蓿花竞相开放的时候。在离地面不远的苜蓿花丛里,成群结队的蜜蜂东奔西忙,时隐时现。
那是八月初的一天,又是一如既往的情景。不管怎么说,临近上午时分,阳光明媚,但天气还不太炎热,高高的天空一片湛蓝,漫无边际,似乎变得越来越高。远近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即使出现一丝,很快又会散去。

一阵阵轻柔而令人惬意的和风拂面吹来。夏日里,风大多从西边刮过来,想必是从大西洋吹拂到无人湾。露水早已散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清晨漫步走过花园时,赤裸的足底也感觉不到地面潮湿,更不用说脚趾间了。
据说,蜜蜂与马蜂不同,只要它蜇了人,就会失去毒刺,并且必然会因此而丧命。 我经常被蜜蜂蜇的岁月里——几乎总是被蜇在赤裸裸的脚上——也多次目睹过这样的情形,至少看到了那个仿佛是从蜜蜂肉体最深处被撕裂出来的、带有三个尖角的镖枪,如此细小,却有强大的自然力,上面凸起某种团状的胶体,也就是蜜蜂的内脏。 此外,我眼睁睁地看着这生灵蜷缩起身子,颤抖,哆嗦,直到停止扇动翅膀。
然而,在这样一个挨蜇的日子里,那只蜇了我这个赤脚人的蜜蜂并未因此而丧命。
当时,关于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刚刚有了雏形。尽管那是一只豌豆粒大小的蜜蜂,毛茸茸的,色彩和斑纹也司空见惯,但它在蜇你时丝毫也没损失毒刺,而且蜇完之后又逃之夭夭了。
这是一次与之前任何一次都毫无二致的蜜蜂蜇人。它猛地一下,使出好大的劲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而且远不止如此,它好像凭借这次行动,浑身上下又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觉得这次被蜜蜂蜇也没什么不好,不只是因为蜇我的蜜蜂活下来了。其中还有别的原因。
首先,人常说,蜜蜂蜇人跟马蜂或大黄蜂蜇人截然不同,有益于身体健康,可以治疗关节病痛,增强血液循环,或者诸如此类的好处。可像现在这样蜇一次,恐怕至少会让你越来越变得麻木,甚至让毫无感觉的脚趾苏醒一阵子。这又是我的一个想象,年复一年,这些想象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不管用。在一个类似的想象或幻想中,我每一次都赤手空拳,常常从黄土或石灰地里大把地拔出荨麻,无论是在无人湾的花园里,还是远在皮卡第的庄园平台上。
出于第二个原因,我很乐意被蜜蜂这样蜇一下。我把它当作一个信号。一个好信号。或者一个坏的?既不当作一个好的,也不当作一个坏的,甚至一个不幸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吧,反正当成一个信号。
这一蜇给了你启程的契机。告诉你上路的时刻到了。挣脱束缚你的花园和地区。快走吧。出发的时刻到了。
难道我需要这样的信号吗?在当初那一天:是的。这无非又是想入非非或夏天做白日梦吧。
02
时间紧迫感消失了
我收拾好房子和花园里需要收拾的东西,特地也让这里那里保持原有的样儿,一动不动,熨烫了两三件我觉得特别合身的衬衫——在草地上几乎还没晾干——装进箱子里,带上关于这个地区沉甸甸的旅游指南。
这可不比去郊区小屋那样轻而易举。
就在出发前,当我要系上高帮鞋时,鞋带断了;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双配对的袜子;我把三十多张高精度地图翻来翻去,直到发现一张我中意的。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这一次却不同,两根鞋带都断了。我之前系了一刻钟,连大拇指指甲都撕裂了。最终,我将一堆不配对的袜子一双又一双地套在一起,几乎全无分别。突然间,我觉得不带任何地图踏上旅途相当惬意。
突然间,我也从纠缠其中的时间紧迫感里解放了,一种毫无理由的时间紧迫感。它一再侵袭我,不仅在启程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往往尤其令人窒息,而且在即将启程的时刻,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没有任何一刻会比这个时刻更厉害。生命之书?无字之书。梦幻结束了。游戏结束了。
然而,出乎意料:时间紧迫感消失了,变得空空洞洞。突然间,我拥有了尘世间一切时间: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时间。而生命之书:敞开着,实实在在,那一页页,尤其是尚未书写过的一页页在世界之风中闪亮,在这里的大地之风中闪亮,在本地之风中闪亮。
是的,我兴许终于可以亲眼看见我的偷水果姑娘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很快,非常快,作为人,作为完整的人,不只是零零散散的碎片,不只是幽灵似的片段。之前的岁月里,这些片段进入我这双垂暮的眼睛,一再为我指点迷津。大多数时候,她闪现在人群里,遥不可及。最后一次?
是的,难道你忘记了,说“最后一次”就像说“最后一杯酒”那样不合时宜?或者像你允许孩子们玩“最后一次!”(比如说荡秋千或玩跷跷板)后,他们会这样喊道:“再玩最后一次吧!”可随后呢:“那就再玩最后一次!”喊叫着。欢呼着。可话说回来,难道你不是经常听到孩子们这样说吗?是的,但那是在另一个国度里。若果真如此——
那个夏日里,我一本书都没带,甚至连我早上还看过的那本书也留在了书桌上。那是一本中世纪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人生。她自断了双手。之所以自残,是为了让那些不断纠缠她的男人彻底断掉想入非非的念头。(自断双手?这只有在中世纪的故事里才有可能吧?)我也把我的记录本放在家里了,把它们搁到一边,就像我自己把它们藏了起来,强迫自己忍痛割爱,再也不去找它们,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去找,禁止自己去使用它们。
出发前,我坐到花园里,坐到花园中央,坐到唯一一把看上去更像凳子的椅子上,把行装放在脚前,远离花园的几棵树,首先远离那几张桌子:一张在接骨木树下,一张在椴树下,一张在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的那张最大,至少尺寸是最大的。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端端正正,跷起二郎腿,脑袋上罩着一顶旅行草帽。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样子正如油画《园丁瓦利耶》(或者不管叫什么)中的园丁。

在生命后期,保罗·塞尚一直偏爱画园丁,特别是1906年,也就是画家去世那年。在这些油画上,园丁瓦利耶几乎都让人看不到面孔,不只是因为遮住额头的帽子。或者说,我想象中的面孔,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也像被抹去了。此时此刻,在我的意识里,这个坐在花园里的人除了面孔轮廓,其余什么都看不到。
然而,一个什么样的轮廓呢?一个剪影,凭借它,脸庞上那片被它包围其中的、几乎空空如也的画面则表现、表达和传递出某种东西,某种超越了现实中的相貌描绘所能传达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并且呈现出从根本上来说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不折不扣的游戏形式。
要是有可能把《园丁瓦利耶》中的园丁那被我改变的名字翻译成“勇敢者”,而不是“看守者”,不,“照看者”、“守卫者”,或者一言以蔽之——“警戒者”,连同那些似有似无、如同被抹去了的感觉器官,诸如耳朵、鼻子、嘴巴,尤其是眼睛,不就符合园丁瓦利耶的特征了吗?
这样坐着,醒着,同时又像是在梦境里,一种另外的梦境,有一个声音突然回响在我耳际——近在耳边,无法再近。那是偷水果姑娘的声音,一个询问的声音,一个如此温柔又坚定的声音——不可能更温柔,更坚定。
她问我什么呢?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故事已经又过去好久了),没问任何特别的事,比如说:“你身体怎样?”“你什么时候启程?”(或者另一些询问,此时此刻,记忆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问我:“你为什么看上去愁眉苦脸的样子,先生?你到底有什么忧愁呢?”
偷水果姑娘直接面对面跟我搭话,在这个故事里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次。(再说,我怎么能以为她是第一次,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次和我以“你”相称呢?)这其中不同凡响的东西仅仅是她的声音,一种如今变得少之又少的声音,或者也许从始至终就少之又少,一种体贴入微的声音,一种丝毫也不会特别让人担惊受怕的腔调。
但首先是一种忍耐的声音。忍耐既是一种性格特征,也更为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行动,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也就是“忍耐”和“容忍”意义上的声音:“我耐心等待,我忍耐你、他和她——我忍耐任何人,或不管什么事,毫无区别,千真万确,持之以恒。”
一生中,这样一个声音恐怕永远都不会变成别的东西,更不用说会突然变成一个截然相反的声音。
在我看来,只要你听一听绝大多数人的(也包括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女人的声音,都与之完全不同。然而,这个声音无疑始终处于越发沉默的危险中,永远都有可能——绝对不会沉默!
从我的偷水果姑娘嘴里突然迸出这句话,你们这些强权者!多年以后,这声音依然不绝于耳,我心想。
有一个演员,在一次采访时被问道,他的声音是怎样帮助他在电影里去表现各种故事的。他回答说:当一个情景,或者整个故事“拥有完美的整体性”时,他靠的是感觉,这不只是发生在他身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评价一个情景,甚至电影的真实性时,他看重的不是他看到了什么,而是他听到了什么。接着,他边笑边补充道,看重的是什么东西瞬间会让我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再说吧,我的听力非常好。这是我从娘胎里带来的。”他所说的,与偷水果姑娘的声音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03
寂静时刻
那是一个阳光高照的正午。这样阳光高照的正午似乎只出现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
周围的邻居好像都无影无踪了,而且不是昨天才消失的。仿佛他们不仅仅是在夏天移居到了他们位于法国乡间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度假屋或小木屋里。他们压根儿就一去不返了,而且有多远走多远,远离法国,回到他们祖先的故乡,去希腊,去葡萄牙山间,去阿根廷大草原,去日本东海地区,去西班牙的高原,可首先会去俄罗斯大草原。
他们在无人湾的房子和棚屋全都空空如也。
可与之前的夏天不同,在我出发前的日日夜夜里,没有报警装置发出过警报,在那些为数不多、长久以来就停放在那里、已经没了发动机的汽车里,状况也一样。
像黎明前一样,整个清晨里笼罩着一刻接一刻不断蔓延的寂静,它越过一条条边界或无人湾地区的边缘,与其说不时被插曲似的、通常为三节拍式的乌鸦叫声打断,倒不如说更有可能被这样的叫声继续承载着弥漫至远方。
然而,此时此刻,伴随着正午时分到来,这种蔓延于整个地区的寂静却被包围在一阵听不见、从夏日的树叶上也看不出的无声无息的微风里。更确切地说,那是一阵出乎意料、静止不动的气流,一阵向外弥漫、可在你的皮肤上——无论是手臂还是太阳穴上——却感知不到的空气流。树叶纹丝不动,哪怕是极轻薄的树叶,比如椴树叶。
这种寂静一下子沉降在大地上,猛地一下,既柔和,又充满力量,每年夏天仅仅发生在一瞬间。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过程:由于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寂静流,这片之前已经笼罩在寂静中的大地随之沉降或沉陷下去,但那熟悉的大地表面,那起伏不平、高高隆起和承载着万物的大地表面依然保持不变。这种情形发生在听得见、看得见和可感知的世界彼岸。然而它历历在目。
沉陷在大地中,这向来是我的一个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在这一独一无二的夏日瞬间成真了。时至今日,年年如此,至少在我生活了二十五年多的同一个地方如此。
同样在那一天,在启程前往瓦兹省的时刻,在这个久久期盼的瞬间,在这无边无际的寂静中,这种更加寂静的时刻降临了。它一如既往,如约而至。然而,有一些东西却并非一如既往,而是完全不一样了。
当我之后抬头望去时,像往常一样,在我头顶的天空上,我看见一只雕大展双翅,划起一道镰刀形曲线,盘旋而上。
时至今日,它依旧每次都如约而至,成了这一瞬间活生生的图像。
在接下来的瞬间里,雕在空中静静地盘旋。在我的想象中,年复一年,始终是同一只大雕。它飞离与猎鹰、鵟,还有秃鹫和猫头鹰共享的、位于西边的朗布依埃森林的巢穴之地,扶摇直上,盘旋飞行在寂静的无人湾上方,此刻向东 , 在巴黎边缘上来回翱翔。
一如既往,我也看到那只在我头顶上方的鸟儿是一只雕,仿佛特地要在这个确定的地区划定它的势力范围,尽管这或许只是——为什么说“只是”呢?——一只鵟或一只鸢。我一如既往,确信无疑地说:雕。“喂,雕!嗨,你怎么样?Que-ce-que tu deviens?”
与往常不同的是,这只雕飞得如此之低。我从未看见过它如此近在咫尺地盘旋在树梢和屋顶上方。这些年里,甚至有一群燕子也翱翔在高高的蓝天上方,就在离雕下方不太远的地方。然而这一次,燕群却沿着自己的飞行轨迹翱翔在雕的上方。我看到——这也和往常不同——它们不是飞行在自己的轨迹上,而是在高高的蓝天上飞得很低,几乎贴在雕的上方急速地穿上穿下,纵横交错,闪来闪去。
虽说周边地区沉陷下去,以往许多年里,此地每每如此。但这一次,地面连同地下的一切却未保持稳固和隆起状态。在这个地区,我瞬间在其中经历的不是那熟悉美妙的洼地或盆地,抑或我的沉醉,而是一种共同的沉陷,一种不只是威胁我一个人的轰然坍塌。
在那一天,这种梦寐以求的寂静后来真的袭上我的心头,作为一场遍及全球的灾难冲击波,哪怕仅仅一秒钟而已。片刻间,我也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不是想象的原因,而是实实在在、确凿无疑、不可回避的原因:
周围地区如此沉陷下去。此刻的寂静不是指点迷津,而是咄咄逼人,让人哀叹悲伤,是一种危险、可怕和死亡的寂静:可怕的寂静,可怕的凝滞。
这种寂静,它表明过去几个月和几年所发生的一切使人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灾难,不仅在法国,当然这里是灾难的晴雨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可怕。在我看来,现在如此,第三个千年的第二个十年里仍将如此。同样,这种情形在那一个瞬间既听不到,也看不见,又摸不着。可取而代之的是显而易见——别样的显而易见。
瞧瞧那些白蝴蝶吧,它们各自为政,蜿蜒曲折地横穿过寂静的花园。我觉得它们好像会立刻坠落而亡。可接下来:在女贞树绿篱后面,在邻居花园里,响起了一阵叫喊,传到我的耳朵里,如同一声死亡的惨叫。
可别这样说:远离死亡话题吧。这里与死亡毫不相干:叫喊来自年轻的女邻居。她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藤椅里织毛衣。毛衣针扎到手指了。几个星期前,就在女贞花仍盛开之时,那里弥漫着女贞花独有的馨香。我透过树叶,曾看见她坐在同一个地方,身穿一件垂到脚踝的浅色衣服,它紧紧地绷在这个即将分娩的孕妇隆起的肚子上。
与其说看到了她轮廓清晰的外貌,倒不如说那是一种想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看见过她的踪影,直到刚才传来这声叫喊,接着便是一阵笑声。看样子,年轻女子似乎在嘲笑自己大惊小怪的疼痛。
此时此刻,随着这声叫喊,又传来一阵哇里哇啦的哭闹声,又或者是一种呱呱坠地的叫声。只有一个新生婴儿才会发出这样的叫声。沉睡的婴儿被母亲分娩的痛苦叫喊唤醒了。好消息!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呱呱叫。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奶,或诸如此类。
绿篱后一片寂静。我多么希望还能久久地听到哭闹声,即便听上去那样微弱,就像是从一个洞窟里传来的。等着下一次扎手指吧,年轻的绣花姑娘 , 明天同一时间!只是到了明天,我恐怕已经去了完全不同的地方。
04
离别
没什么东西会在那个夏日一如既往?一派胡言:一如既往。一切?一切。一切都一如既往!这是谁说的?我。我决定如是说。我坚定不移地如是说。我表明:一如既往。惊叹号?句号。后来,当我透过绿篱窥望时,我的目光碰到一只大眼睛,仅仅一只眼睛,婴儿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回望我。我试图也有样学样。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就这样,每年到了这样一天,总有一只蜜蜂会第一次蜇到我;就这样,以同样的方式,有一对小蝴蝶会如约出现在这里,取代了一群七零八散又大又白的蝴蝶,一如既往。

我把这对小蝴蝶称为“巴尔干蝴蝶”。它们之所以获得这个名字,因为它们成双成对飞行,形影不离,显得与众不同。当年我在巴尔干原野上漫游时,这种现象曾经屡屡映入眼帘。这又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然而,我之所以采用这个名字,或许也可以归因于两个小玩意儿看上去一点也不显眼。它们时而晃晃悠悠地飞去,时而完全悄然无声地落在郁郁葱葱的草丛里,让人难以识别出来。
是的,一如既往,此时此刻,这样一对巴尔干小蝴蝶今年第一次在这里相互追逐,翩翩飞舞。一如既往,它们翩翩飞舞时让人可以看到那与众不同的优雅,至少我未在任何别的一对蝴蝶那里发现这样的情形。这是一种上上下下、纵横交叉的飞舞,同时又分别如此相宜地就地停滞一阵子(接着又在别的地方同样继续飞舞)。
在这个过程中,两只小蝴蝶一个劲儿地回旋飞舞,形成了一个三体形象,让你看得眼花缭乱。任凭你怎样去观看,也难以分辨清三体合一的图像。而且你心里也明白,在这其中,你看到的不过是两只真正的蝴蝶在那里彼此翩翩飞舞:不可能,浮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不可分离的三个形象。
像此时此刻一样,我从凳子上站起身,紧随两只飞舞的小蝴蝶,保持平视,要把这神奇的现象看个究竟:径直就在我面前,几乎离我的眼睛仅有一拃远,两只蝴蝶彼此嬉戏,互相绕圈,互相缠绵,难解难分,三体合一,让你看得晕头转向。虽然它们突如其来,也许会瞬间分离开来,清清楚楚地呈现为两只,甚至彼此不和,各奔东西。但是片刻间后,它们又旋转着从眼前飞过,变成了三体合一的图像。
然而,它们为什么要分离开来?它们为什么要让人看看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儿,也就是两只而已?啊呵,时间。大量的时间。
我坐下来,继续观看这一对蝴蝶飞舞。啊,两只飞舞的蝴蝶变成三体合一图像时总是闪闪发光。美好的一天,巴尔干。嗨,你们告诉我吧。你们会变成什么?旅程快乐。——为此,我后来第一次发现,两只小蝴蝶飞舞时不断快速地变换位置,这多么像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人行道上广受欢迎的小帽子游戏呀。骗局?幻觉。——又是为此:果真如此的话。一切顺利。
现在出发吧!之前依然是一圈习以为常的告别,绕着房子,穿过花园,时而也会反方向走。
习以为常?这一次,我走了一圈,其中没任何东西可以说习以为常。或者:我围着房子转一圈。当我考虑到长时间不在家时,常常都会这样。然而,我这一次围着房子转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前所未有,情不自禁,油然而生:一种离别的痛苦,虽说一再出现,但此刻已经强化为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
本文摘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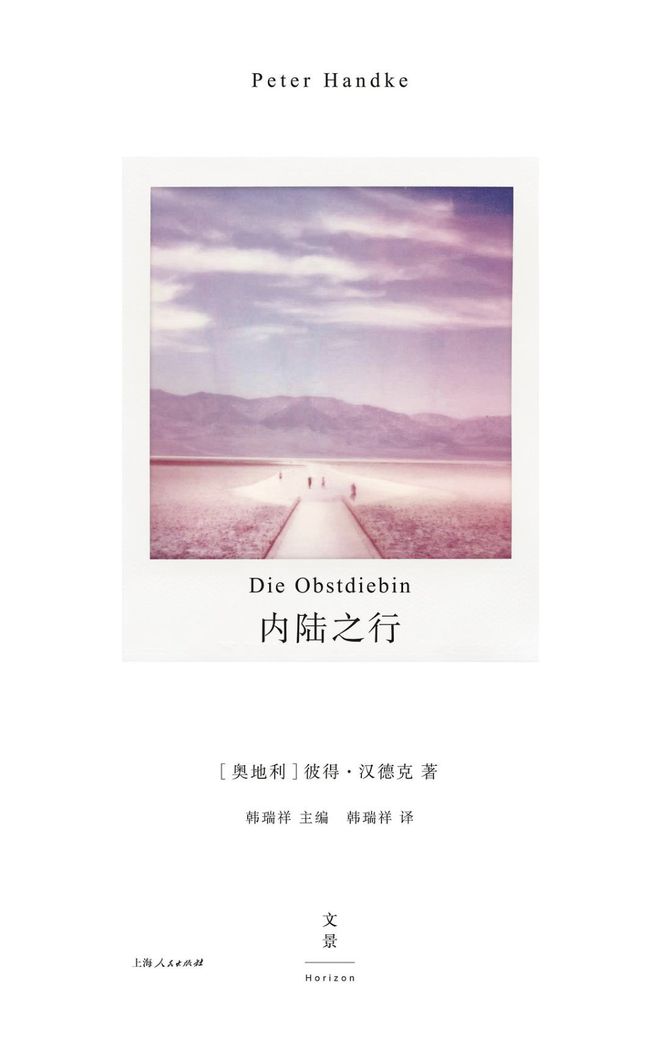
《内陆之行》
作者:[奥] 彼得·汉德克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韩瑞祥
出版年: 20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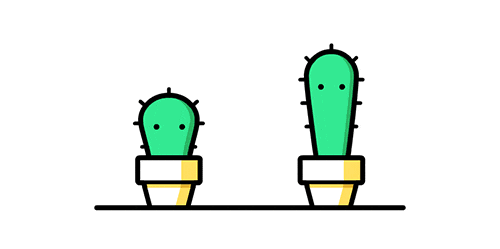
编辑 | 轻浊、刘洁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彼得·汉德克:我在森林,也许迟到……》《托斯卡纳艳阳下》《明亮的星》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