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姜文的审美是“离群值”——远在大数据曲线以外

陈冲最为大众熟知的身份,自然是电影人。她出演的《末代皇帝》《太阳照常升起》,已成为影史经典,然而,她同时也是一位严肃的写作者。在她最新出版的自传性散文集《猫鱼》里,陈冲从祖辈的往事,写到家人,写到自己的少女时光,参演电影的经历,以及自我的成长。
下文选自《猫鱼》中有关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一篇。陈冲回忆参演姜文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她一开始羞于念出林大夫的台词,因为“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但随着姜文的引导,她逐渐认识到林大夫这一角色的魅力,“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她说,“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本文摘选自《猫鱼》,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太阳照常升起》,
就是源自主观的记忆和想象
我给姜文发微信:我想写一篇参演《太阳照常升起》的文章,你有什么可分享的资料吗?刺激或提醒一下我的记忆。
他回:暴雨天到上海去邀请你,我装模作样地谈着故事……

与姜文在威尼斯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俩在兴国宾馆聊天。我依稀记得湿土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巨大的雨点敲击着一切,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亮一片青草,雷声隆隆响起,天色渐渐暗下来……聊了些什么却已淡忘。我有模糊的印象,他买了一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但完全不记得他邀请我去演里面的什么角色。我怎么会记得天色和气味,却忘掉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他记错了?
好像是博尔赫斯说的,我们是我们的记忆……那个不断变形的幻想博物馆,那堆破碎的镜子。从逝去的时间里,记忆只选择某些碎片,我们似乎总是在企图用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现实,而记忆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在发现,而是在隐藏事实。
我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影片里四个证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但都同样可信,从而破坏了我们对绝对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来心理学家们用这个概念发明了“罗生门效应”这一科学名词,来形容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
其实《太阳照常升起》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主观的记忆和想象。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是在姜文的工作室——一栋坐落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内的红墙房子。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文化人民劳动宫”。门前种着常青树,院子里似乎总有些跳双摇、挥高尔夫球杆之类的活动,厅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每次我去,大家都会做起平板支撑、俯卧撑、瑜伽,或者什么其他时髦的健身动作。我常会被叫出来跟某个陌生的小伙子比赛俯卧撑——我每撑一个,他得撑五个。小伙子一般都会上当,因为我那时候能一口气撑二十个,女人里挺少有的。

摄影:Russel Wong 黄国基
那一天,姜文带我进了他的放映室,让我坐在一张舒适柔软的单人沙发上,嘱咐身边的人拉上窗帘,开始讲他脑海里的一部电影。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半坐半躺在另一张沙发上,闭着眼睛形容起一个村庄。一会儿,我也合上了眼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的声音——
……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呢?那种旧黄色的墙,和头发色儿的草顶。我们一般看到的草顶,是变旧的,是黑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村庄有些新草顶。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时是黄的,但是这草在黄之前,它还绿过。所以还有嫩绿的草顶,甚至让我们觉得这草顶是活的。
有些草顶上可能站只鸡,有些草顶上永远有只鸡,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在上面了。还有徽派建筑式的房子,白墙黑瓦;还有像吊脚楼似的,全木结构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已经被错落地放在村子里面了,似乎在有人住之前,这村子就已经这样了。
……这村儿有雾,雾到什么程度啊,不是每天有。一旦有的时候,就像眼前的追光似的,随着人走,有一个直径四五米的范围。你往前走,所有的东西就像舞台穿过追光一样渐显,通过你再渐隐。
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尤其动物呢,经常是一头驴,一头牛,似乎它们不是为了干活的,一直到蹄子那儿都是干净的,焗了油,而且色儿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驴,可能是黄色的驴,可能脖子上这两道是红的。总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没有那种扎眼的不一样。
第一印象是熟悉,对,比对还对。第二印象开始发现,哎……这驴是见过,这色儿没见过。于是渐渐开始有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植物也是这样,可能有一种像滴水观音似的植物,但是上面长着西红柿……你让小孩画一张画,他会特别自然地把植物安排在他想要的位置,但跟实际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包括颜色。这个分寸在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不能立刻让人猜疑,一定要是第三第四眼的时候,已经认可了,已经熟悉了,也已经上当了。
另外呢,雾还分上下层,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脚,看不见头;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胸,看不见脸和脚;有的时候,看见脑袋,看不见人。这雾还能走,这块是平的,另一块“唰”就过去了。所以随着人的视线在雾中走的时候,除了动的东西渐隐渐显,静止的东西也渐隐渐显……
不知过了多久,姜文的声音停了下来,我慢慢睁开眼睛,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道金色的夕阳,屋里的几个人如梦初醒。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动,感到一种莫名的特权,好像有人跟我分享了他最难以名状的欲望和最原始的恐惧——他潜意识里的私密仙境。那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也不完全陌生,仿佛梦里见过,仿佛我被另一个人梦见了。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发信说,姜文要开拍新戏了,他想请你参演。我问,剧本呢?经纪人回,姜文说你已经听过了,他说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非你莫属的角色。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天听到的故事里有哪个角色是非我莫属的,但是我二话没说欣然应邀——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出发前一天剧本终于寄到了,摸上去很薄,好像最多二三十页。打开一看,里面的一张条子上写着:这是电影四个故事中的第二个,你的角色是林大夫。
第二个故事
一九七六年·夏·东部
76.日 外 校园
歌声继续。
从金色中渐显变亮。
这是一所大学,校园宁静,整洁,人迹罕见。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老舍依然古气,老楼依然洋气……
林大夫就在这个宜人的校园工作和生活。故事简洁、诗意,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像一种神秘的速写,隐喻着更复杂的经历。林大夫与老唐(姜文)有染,心里还暗恋着梁老师。我只是一路纳闷,姜文怎么会认为我是林大夫呢?她是我们上海人骂“十三点”“花痴”的那种女人。我在生活中十分克制,自认为跟那样的人相差甚远。
回想起来,林大夫的有些特征,或许是我给姜文的某种印象。比方我从来没有吹干头发的习惯,有几次洗完澡直接去了他工作室,头发还是湿的,他会说,湿漉漉的真新鲜!剧本里林大夫的头发和她的一切也永远是那么湿漉漉的。
还有一场戏,林大夫双手扒着二楼的窗台,笑盈盈地跟另一扇窗台上吊着的梁老师说:下面有草,松手跳下就行,我先走了。说着她就消失了。几十年前——我们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姜文和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个什么活动,结束后我带他到新搬的家里去玩。停下车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忘了带门钥匙。房子在山坡的树丛中,我爬上了一棵大树,然后跳到屋顶上,再从另一边爬到了客厅的阳台,从落地窗进了客厅。不记得那晚姜文是跟我一起爬的,还是我先爬进去,开了门让他进来的。也许姜文让林大夫爬窗,跟那次的经历有些潜意识的关联吧。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到达昆明的时候,大部队还在另一个景点拍摄,我独自逛了两天街。在邮件里我告诉丈夫,“昆明的空气比上海的要清爽许多,气候也四季如春,有些像旧金山,但是更滋润一些。老城的窄街上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还有从尼泊尔来的耳环手链。我给孩子们买了手绣的布鞋和银手链,给自己买了像一串串迷你葡萄那样的绿耳环,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能为你买的东西,明天再去找找,希望能圣诞节前赶回来给你们”。
02
人总是恐惧自己所向往的,
向往自己所恐惧的
拍摄《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和我只同演过一部《茉莉花开》。当时他是客串,我演一配角,好像只有一场戏跟他同框。有一天他拍完了自己的戏,在一旁看我,提醒我说,身体别泄着,挺起胸提点儿腰。我天生有些驼背,一辈子都在纠正,大多数人感觉不到,但是他马上观察到了。
我进组时《太阳照常升起》已经开拍两个月,演职人员都已进入状态,而我初来乍到,心里完全没谱,所以非常紧张。姜文随意地让我把林大夫的台词念一下。我一开口就感到脸红耳热,磕磕绊绊地完全不知道该使什么劲。姜文眼里流露出不可名状的疑虑,好像我跟他记忆里的人有出入。
那天我给丈夫发了邮件:“今天我让导演失望了。那些台词的分寸太难把握了!你知道我的脸皮多薄,很难在一个陌生的化妆间说演就演。而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我需要找到自信,好在这个礼拜不拍我,只做试妆造型……”
在服装间试衣服的时候,姜文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小时候我们大院,有个像林大夫这样的阿姨。她三四十岁,皮肤好身材好,鼓溜的,是一个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这个阿姨跟孩子说话,或者给个糖,或者胡噜胡噜头的时候,孩子会被家长拽到一边,说,别理她,她是妓女。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妓女,但心里会“咯噔”一下,而且从此开始明白妓女是怎么回事。没人解释过,都是无师自通。她衣服里隐约透出胸罩的带儿和三角裤,白布的胸罩带比现在的那种宽,从肩膀下来是反着的“八”字……
这故事提醒了我,那些男孩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内衣,他们也记住了她是“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
一天姜文拍完戏后来到服装间,看见我在镜前试衣,皱起眉头说,这是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啊。我身边的造型设计、服装师、化妆师都有点蒙了,林大夫不是就该穿医院的白大褂吗?姜文接着说,我要的是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那件白衬衫。屋里的人都警觉地体会着他的意思,但还是茫然。他接着解释,就是那种一眼看上去是件医院的白大褂,但其实完全不是。你们回去看看《罗马假日》,体会一下那种漂亮,帅。他指着白大衣的下摆说,“冲美”腿上的肌肉好看,你们得把这衣服剪短了,但又不要太短,正好露出一点膝盖上面的四头肌。姜文那些年叫我“冲美”,后来组里年轻人也跟着这么叫。
两天后我们重新试改过的白大褂,姜文又提出了他对袖口的想法:袖口不要纽扣,要露出半个小臂,但不要圈起衣袖,而是那种四分之三的袖长,开着点衩……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导演如此细腻、如此具体地设计服装。在日后的拍摄中,这件姜文记忆里、想象中或者梦里的白大褂,成了我的隐身服、林大夫的红舞鞋。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的第二个故事,是由一桩“摸屁股”事件展开的。学院广场上放露天电影《红色娘子军》,银幕上一对女兵跳起双人舞,她们的腿冲着镜头朝天踢着,越踢越近。银幕正反面都是人,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站着。当女兵踢高着腿跳到镜头跟前时,突然有人喊“抓流氓啊!”全场一片混乱,正在看电影的梁老师也莫名地跟着人群逃窜,最后被抓住了。林大夫自告奋勇地说自己被摸了,为的是要“救”她暗恋着的梁老师。
为了确认罪魁祸首,院领导老吴让林大夫站在一块白被单前面。隔着被单,嫌疑犯们被编了号,挨个上前摸林大夫的屁股。她如果认出哪只手是看电影时猥亵她的,就叫停。
95. 日 内 校办
林大夫从一片白中渗出,渐渐清晰。
林大夫看上去新鲜,美丽,端庄,湿润,呼吸略微急促。
屋里气氛安静,肃穆,庄严,紧张。
有风,林大夫的白大褂,她身后的白布帘被风轻微鼓动着。
白布帘后
林大夫,准备好了吗?
林大夫
准备好了。
白布帘后
开始?
林大夫
开始吧。
“预备—开始!”我撅着屁股坐在白被单前,全组工作人员屏息凝视,我突然窘迫。姜文见我有压力,笑嘻嘻地说,你觉得这是一件特刺激、特好玩的事,一会儿凝神细品,一会儿忍俊不禁那种感觉。我发现姜文说戏总是那么简单、具体、可行,而且他的选择也总是那么意外、有趣、脱俗。
摸完一轮以后,老吴宣布测试结束。我从带轱辘的椅子上“噌”地站起身,说,那天看电影我是站着的,跟坐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能不能站着再试一次?演完一条以后,姜文说,你把椅子踢一边去。我绷直了腿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椅子,它慢慢滑向一边,像一名依依不舍的舞伴,把我一个人留在聚光灯下独舞。不知是肢体动作让我感到风骚,还是风骚支配了肢体动作,空气里仿佛弥漫出浓郁的男性荷尔蒙……
拍完后我去监视器看回放,屏幕里这人虽然脸熟,但也陌生,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姜文说,这就是你,平时你老爱装正经。
从第一次读剧本开始,我一直在为第九十九场感到为难、发怵。在这场戏中,我将厚颜无耻地向梁老师求爱。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期待能像林大夫那样,裸露一次欲望?人总是恐惧自己所向往的,向往自己所恐惧的。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99. 夜 内 病房
梁老师躺在床上凝视窗外。
胡子已被老唐送来的剃刀刮净。衬衣也换了。
打着石膏的腿架在床上。
轻轻地,门开了。一个女人闪进来——是林大夫。
头发仍然湿漉漉的,面色有点儿白。
只见她迅速转身将门锁上。
林大夫
这里的大夫我都熟悉。
声音在喘息。碰壁顿生些暧昧和朦胧。
轻盈地,她走到梁老师的床头,很职业地挪了挪那条有石膏的伤腿。
她的影子摩擦着梁老师的脸。有水珠从头发上滴下。
梁老师无喜无悲,看着继续喘息着的她。
林大夫
我不能多待,跟你说几句就走。
梁老师无语。
林大夫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救成你,但,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会跟你一块儿承担。
梁老师
那天,你根本没有去看电影,为什么要出来指认我?这是什么把戏?
林大夫
连你都上当了?!哈哈……我就是要引火上身,然后再道出事出有因。我得先让他们认定——是你摸了我,再让他们醒悟——我对你有感情……
梁老师
有感情?你应该早表示,为什么单单挑这个时候?
林大夫
问得好!问得好!这个时候是最能救你的时候。我早就设想好了,你一摸我,我就大叫,就等他们最后问你那句话:“梁老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梁老师
就算他们问了,你又能怎么样?
林大夫
他们要是这么问,我就立刻转身扑向你,一把搂住你!大声说给他们,我爱他!我应该被他摸!我是他的人!
说时迟那时快,林大夫已顺势搂住了梁老师。
梁老师轻闪一下,也无济于事。
林大夫
可惜,可惜。他们竟然少问了一句关键的话。老吴太愚蠢!对不起,我没救成你,但是我想救你!放心!我会继续想办法。一定让他们最后明白你摸的就是我。他们不能抓走你!知道吗?那天你一碰我,我就立刻闻到是你。什么手软不软之类的话,都是骗他们的!每当你来医务室,我老远就闻到了你,你还没进门,我就难以自制,就得深呼吸。离我十米远,我就开始脸红。两米远,我就心跳加速。那天给你包扎手指,你晓得我有多么难?你离我太近!闻到你,我心慌,胸闷,随时都要昏倒,就像,就像一下子得了各种病,可又不难受,甚至幸福,甚至快乐。那天,你就在我身后,又离我那么近,你的手一摸到我……我就不行了,就想立刻栽到你怀里……
梁老师
林大夫,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在我看来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林大夫脸色一变。
林大夫
梁老师,我必须告诉你,感情不是分析出来的!你未免太冷静了!再见!
说罢,扭身就走。门被重重地关上!可瞬间门又打开,林大夫迅速返回。她像换了个人。和蔼可亲,善解人意。
林大夫
我知道,我知道,你实在不放心我。其实你的心里跟我想的一样,你紧张,你羞涩,你不好意思。这些我能理解。现在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在表达感情,可是,我敢肯定,我同时也是在替你说出你心里的话。对吧?我一离开你,脑袋里就全是你。刚才我本来想走掉的,但我不能那样离开,我怎能让你再受伤害呢?(停了一下)可我又不能老坐在这里,闻到你,我就说不出来的激动……不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肯定会休克,我一休克就跟死了一样。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林大夫意乱情迷,语无伦次。她害羞,激动,手捂发烧的脸。
林大夫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说了。我心跳得厉害,胸闷了,胸闷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必须走了!
林大夫说着就朝门边退去。消失前说了句:我会再来看你!
这可怎么演?拍摄那晚,我们在现场走了几次戏,姜文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宣布停拍。夜里我给彼得发了邮件:“结果今晚什么也没有拍成。现在刚过了夜里十二点,我们一个镜头没拍就收工了。导演对服装不满意,不过说不定是走戏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对。停拍也好,也许明天我会更有把握一些。这场戏至关重要,也非常难演,我祈祷上帝不要让表演的精灵弃我而去。我觉得我是为了这场戏而被聘请来的,它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想做到淋漓尽致,但我没有信心能够达到。”
停拍后我们回到服装间,姜文翻看着那里的各色布料,说,图案得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又要干干净净的。外面穿的雨衣得透明到跟没有一样,而且不要那种软绵绵的塑料布,要挺拔有型的。“的确良”的裤子,要接近“冲美”的肤色,有笔直的裤缝,挺得像两把刀那样。
第二天,新服装做好了,非常好看合身——黑底白圈圈的衬衣、全麦色的裤子和透明的凉鞋。望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像记忆中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我走进现场的时候,姜文在看着镜头,跟摄影师讨论着墙上的光影,路灯透过玻璃窗外的雨水和白帘照进来,几何形的影子在墙上波动。工作人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着雨水滑落的速度和流量。
姜文看见我进屋,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满意了。排练的时候他说:“记不记得那些得了奥斯卡奖的演员在领奖台上的样子?那种一面哭一面笑,喘不过气来的激动样子,同时还被自己的激动所感动?”我一听就乐了,马上明白了该使什么样的劲。记得他还给我听了一段意大利歌剧,好像是普契尼作的《贾尼·斯基基》中的《我亲爱的爸爸》。那是一个女儿在煽情地表达对父亲的爱,夸张得有了喜剧感。这段音乐让我从另一层面感到了他想要的基调。
终于一切就绪,我浑身滴着水珠,在暧昧、缠绵的光影中,从门口无声地闪了进来。此情此景让我感到某种原始的渴望在身体里流动,一泻千里的倾诉欲油然而生。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了几分钟,但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完全不是预期的那样。一气之下我转身就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梁老师刚要松一口气,我又开门回来了。这一关和一开之间的节奏、情绪变化没有任何过渡。排练的时候,我按自己的习惯、套路,撞上门,下一秒再推开,有个自然的停顿。姜文说,你在“砰”关上门的同一秒就开门回来,越快越好,进来跟换了人似的。
一开始这个节奏对我有些“不自然”,但我选择去信任姜文的直觉。拍了两条以后,我开始看到这个动作的独特和精彩——好比在听音乐的时候,期待中的两拍“啪——啪”意外地以一拍“啪啪”出现,熟悉的音符便瞬间传递出全新的感情,给人惊喜、触动。林大夫的那股子劲,就是通过踢椅子、关门开门这些小动作,变得栩栩如生、独一无二。作为一场幽默的戏,这样演也是更有效的节奏。

《太阳照常升起》林大夫剧照
一场五分钟的戏,几乎全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如果姜文没有让化、服、道、光影和摄影机为我抒发,如果他没有启发我对气息与节奏的运用,它会多么无趣甚至难看。
03
姜文的审美是“离群值”,
远在大数据曲线以外
两年后看完整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剧中的三个女演员,各自有这样一段长达几分钟的独白。周韵的那段,是在一间巨大的、荒废了的厂房里拍的。太阳从破旧的窗口照进来,水泥地上一块一块的光,空间里却是幽暗的。她挺着大肚子孤零零站在当中,头顶莫名射下一束舞台的追光,照在她身前整齐排列着的遗物上。摄影机不停地围着她兜圈,让人感到天旋地转——这是一个将要疯掉的女人,在跟死去的、移情别恋的丈夫倾诉。
孔维的那段是在新疆的戈壁滩上拍的。层层叠叠、无边无际的沙丘上,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夕阳里向我们走来。一阵铜铃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然后我们才看清她是谁。骆驼背上,孔维身着西装头戴草帽,在跟周韵讲述着自己的未婚夫——他如何不要脸地勾引她、爱她。笑声在浩瀚的沙漠回旋,说着说着大朵大朵的雪花开始飘落。这个从南洋嫁过来的女人,在她人生的第一场大雪中,憧憬着与爱人的狂喜。
是姜文的电影“炼金术”,使这三长段的独白在银幕上歌唱和荡漾起来,令人感到文字以外更神秘和抽象的寓意。他的审美是“离群值”——远在大数据曲线以外。他对演员的观察也比绝大多数导演更为细腻、敏感和准确,而且是投入了感情和想象力的。他发现到我们各自独特的、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活力和能量——那些如果没有在这部电影中释放出来,就无人知晓的宝藏。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周韵
后来,我因为扮演林大夫得到了“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配角,和“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我跟姜文说,我在戏里的每个眼神、喘息、扭动都是你挖掘出来的,你是我见过最会讲戏的导演之一,或许都不是“之一”。姜文说,哪儿啊?我不记得跟你讲什么戏啊,是你自己演得好。看来在记忆面前,我们的确都是“不可靠叙事者”。
拍完第九十九场后,我只剩下最后三场很短的戏。
109. 日 外 医务室
老唐和梁老师路过医务室。
老吴的歌声也尾随而至。
林大夫高高地坐在石阶上,腿间一个大白盆,她正在洗衣服。
笑盈盈地,林大夫的目光迎接着老唐和梁老师。
林大夫
有好事吧?我刚才听见《万泉水》断了一会儿。看来不用我帮忙了。
老唐
洗完了放那儿,待会儿我来帮你拧。
林大夫跟梁老师的目光碰上,没躲闪。
她嘴角浅笑,低头,接着洗。
111. 日 内 走廊
两人刚到门口,就听见楼道里传来了林大夫的脚步声。
老唐和梁老师躲在门口,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着走廊那边。只见林大夫拎着一个网兜,里面放了吃的东西,来到老唐家门前。她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然后像跳踢踏舞那样,嗒嗒嗒嗒!很有节奏地用鞋跟敲击了几下地面。
声音清脆悦耳。
这边老唐和梁老师,见到此情此景,突然笑出了声。
林大夫先是一愣,扭过头来看着他们两个。
林大夫
讨厌!快来开门!
老唐和梁老师走了过去。
门关上了。
钥匙挂在门上,轻轻晃动着。
房间里传来了吉他的声音,继而传来了《梭罗河》的歌声。
中间还夹杂着小号干扰的声音,以及在伴奏时三人的说笑声。
他们在里面笑着闹着。
镜头只在门外,静静地靠近,门再也没有打开。
只有里面的声音在唱。
画面黑去。
歌声却没有停下来。
在这两场戏里,林大夫的样子坦然快乐,好像在病房里跟梁老师求爱未遂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拍完后我悟到了,她从来不让男人感到歉疚,这是她可爱的地方。我似乎总是这样跟角色擦肩而过,回眸时,才看清楚演的是谁。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我拍的最后一场戏,是梁老师在终于讨回公道后自杀了。
112. 日 外 操场
歌声继续。
画面亮起。
在一个水塔之上,梁老师高高挂在那里。
一根枪的背带套在他的脖子上。
他衣着整齐,样子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
他的嘴角甚至还带着笑意。
镜头向下摇去,很多人在下面仰着头望着高处的梁老师。
林大夫,老唐,那个陌生女人,还有食堂的那几个女孩,他们都在。
他们的眼神,有的不理解,有的惋惜,有的含着泪水。
电影上映后,有些观众企图用因果逻辑去解释梁老师的死——有的说是林大夫害了他,有的说是老唐害了他,或者是他俩联手害了他。其实这事跟三个人的关系毫不搭界,他们仨都是这个荒谬世界的一分子而已。正如加缪在《局外人》中阐述的存在主义哲学那样,梁老师选择死亡,也许是他认识到了世界之荒诞,人之无能为力,生命之无意义。
二○○五年圣诞前夕,我归心似箭地坐上了回家的飞机。当我俯瞰云层下渐远的翠湖时,突然觉得这个梦还没做够,这个约会还没完,甜品还没来得及上……我曾每天沿着湖边,走去云南大学拍戏或者看姜文导戏。湖面上飞的不是野鸭,而是江鸥,让人觉得异样。云南大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让我联想起记忆里上海医学院的院子和楼房。那是我梦中常去的地方—母亲穿着白大褂,带我去实验室的动物房,教我用水管冲洗两个很大的笼子和里面的猴子。它们跳到笼顶倒挂着躲水的样子很可爱,忧郁的母亲笑起来,她的笑声在我心里漾起层层涟漪。
我想起云大那栋朱红漆的木建筑,从骑楼上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大树、草地和野花,那么赏心悦目。我们在那里拍戏时,云大的一位领导过来看我们。我问他,这楼是什么年代盖的?那么好看。他说这是原校址的一部分,有近八十年历史了。然后他的目光变得遥远,沉默片刻后告诉我,他学生时代曾经住在这里,当时全校最美丽的一名女同学,就在这栋楼里被强奸和杀死了。他重复地说,她真的很漂亮,舞也跳得很漂亮……
04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让你联想起生与死的电影
二○○七年,《太阳照常升起》被提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我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再次见到姜文,他比拍戏时显得年轻许多。戏中未曾与我同框的周韵、孔维也在那里欢聚一堂。威尼斯是我此生到过最美丽的城市,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造的建构能跟它比拟。我依稀记得那里纵横交错的水道,映照出黄昏的彩云和古老的建筑;夜幕降临时,姜文、周韵与我和丈夫穿过一座千年石桥,行走在圣马可广场上,无数白鸽在半空盘旋着……
我一般不能忍受自己在银幕上的样子,参加开幕式经常是到个场,灯一暗就溜出去,但是《太阳照常升起》属于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我只参与了电影四分之一的工作,很想看到完整的作品。
坐在影院里,我被姜文惊人的才华、勇气和野心所震撼——他企图用梦的逻辑,来叙述两代人在“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故事。人做梦时是最本质、最忠诚的自己;在梦里,我们的阴影最黑暗,创造力最狂野;在梦里,我们建筑和拆毁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无须对任何人解释;冥冥之中,一切魔幻、荒诞、意味深长。
影片的时空是自由和不连贯的,前三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各有一个不期而遇的死亡:1.疯妈(周韵)消失了,她的衣服跟个活人一样顺河流漂向尽头;2.梁老师上吊了,蓝天下他双手插着裤兜,仿佛在微笑;3.疯妈的儿子村长被老唐用猎枪击毙了,村长似乎觉得值,因他睡了唐妻(孔维)。第四个故事则是这些人物十八年前对生命的狂欢,对未来的憧憬。
的确,是死亡成就了生命。正因为三千多万年前的变形虫、细菌、藻类植物有了死亡的能力,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存在。我再次感叹,生命是多么偶然的奇迹——如果大爆炸产生的反物质比物质多一点,如果地球的轨迹离太阳更近一点、或者更远一点,如果你的母亲在另一个夜晚受精……你都不会在这里。所以,就连死亡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要战胜怎样的赔率,才降落到了人间。
《太阳照常升起》是这样一部让你联想起生与死的电影。
十五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那座奇异的村庄,回响着一个女人重复地叫喊着“阿廖沙”的名字;那个空荡、干净的校园,飘荡着“美丽的梭罗河”的歌声;那片戈壁滩上的大雪和星空……
闭上眼睛,我依然能够看见电影辉煌的结尾:沙漠上熊熊的篝火,姜文和孔维的婚礼正在狂歌狂舞中举行着,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燃烧的枝叶飞扬在空中,飘向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周韵在上面看着远处沸腾的人群,星星点点的火光向她飘过来;她蹲在火车的蹲坑上,起身时发现大肚子没有了,低头看到坑里飞速向后的轨道,悟到腹中的婴儿从洞里掉下去了。

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
地平线上,列车慢吞吞停了下来;周韵沿着铁道往回狂奔,跑着跑着荒原上长满了绚丽的鲜花;万花丛中的铁轨中央躺着新生的儿子。此刻,太阳升了起来。生命——跟爱与死亡一样,跟日出日落一样——势不可挡。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命运,一切终将无法挽回,他们此刻对生命的喜悦和憧憬也因此变得更加壮丽、浪漫、神圣。
姜文自己对《太阳照常升起》并不满意,他认为还没有把脑海里的那部电影完美呈现出来。我也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瑕疵,总觉得我的能力远不及我的雄心。
记得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叫《玛莎》的传记,作者德·米勒是一名编舞师,她在一九四三年被聘为音乐剧《俄克拉荷马!》的编舞,首映后一夜成名。德·米勒非但不觉春风得意,反而倍感沮丧——评论家和公众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她呕心沥血的创作,却突然把她认为“只是不错”的一个作品誉为她“绚丽的成功”。
一天,她在剧院餐厅遇到伟大的舞者玛莎·葛兰姆,聊起自己的感受。德·米勒说,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只能看到缺陷和错误,没有满意的时候,难道我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感了吗?玛莎·葛兰姆说,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满足感,唯有一种神赐的不满和幸福的骚动,驱使我们继续前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活力。
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这段对话。
速度和大数据把所有的传媒压缩得扁平、即时。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各种视频画面冲击,它们不请自来,占据我们生命的每个缝隙,但有多少能让我们日后铭刻在心?
生活在这样朝不保夕的速度和数据中,叙事——与任何其他艺术一样——也许是人类延缓时间、逃避死亡的途径?那些晦涩的情节或者有趣的题外话,也许都是为了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一条直线是生死之间最短的距离,那叙事应该是一座曲径通幽的迷宫。《太阳照常升起》是我去过的最诱人的迷宫之一,那里时间天长地久,我们不需吝啬,可以悠闲自在地迷失、探索、迂回、发现、思考、隐藏……
本文摘编自

《猫鱼》
作者:陈冲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年: 20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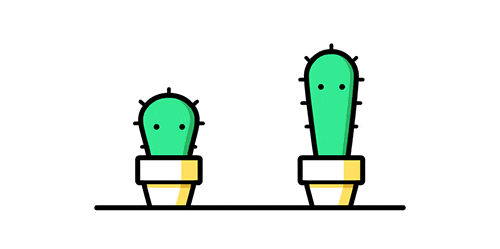
编辑 | 轻浊
主编 | 魏冰心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